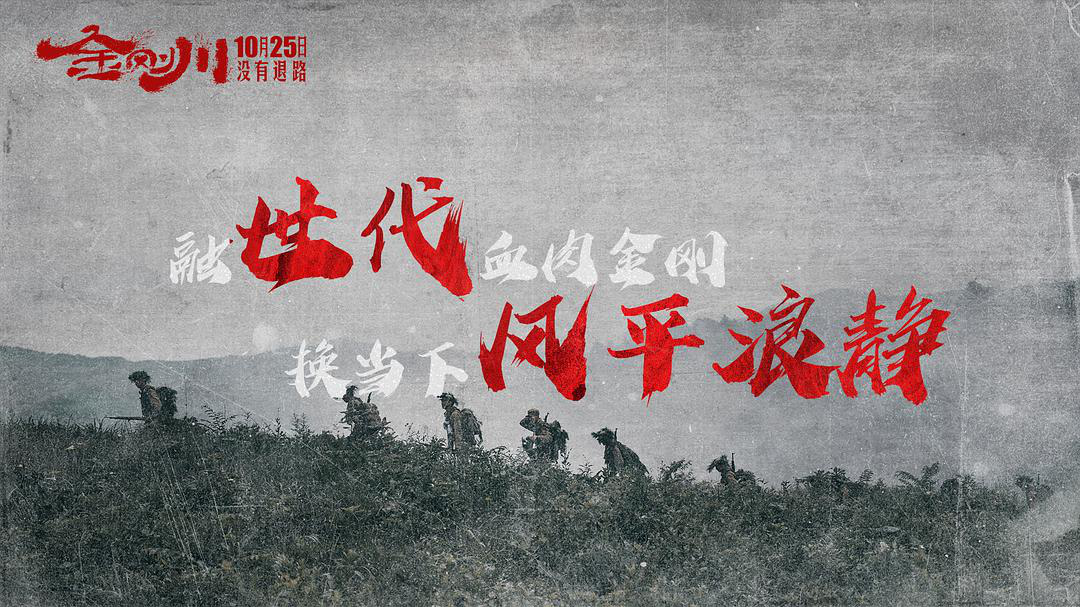诚然5000万成本的大投入可能不捅破文艺片受众的天花板破出边界去,要回本会很难,但这样的营销,是否对一个导演真正负责?当他找到属于他的观众,电影才能够得到公允的评价。
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推到大众面前,承受无端骂名,下一次又是否会影响他的创作和下一部投资方对他的判断。
来源丨整理自新京报、澎湃新闻、百家号
由毕赣导演,汤唯、黄觉主演的电影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于2018年12月年31日在全国公映,片方之前打出的“一吻跨年”的营销,让这部文艺片首日预售票房高达1.59亿,超过了《速度与激情8》等好莱坞商业大片,最终首日票房达到了2.64亿。
然而,首映当天,第一批看过电影的很多观众却在网上留下差评,打一分表示对电影的不满,观影过程中更是有很多观众中途退场。据猫眼专业版显示,2018年12月31日,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大盘退票人次为31.9万,大盘退票率为4.4%,远高于同档期影片《来电狂想》1.2%和《海王》1.0%的大盘退票率。

经过首映当天出现的大量差评,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豆瓣评分从之前的7.5分降到现在的6.8分,随之全国院线排片也从首日的34.1%降到第二天的13.7%,上座率更是从46.4%降到6.3%。2019年1月1日,截至发稿前,该片上映第二天的票房为1088万,当天票房排名第5,票房跌幅高达95.8%,这个纪录恐怕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独孤求败了。

大部分被营销带进影院的观众,或许不熟悉毕赣,也没有看过毕赣早前的《路边野餐》。他们在看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宣传片和简介时,可能还误以为这会是一部“好看”的悬疑片。
影片开头写着“致观众:这不是一部3D电影”,拿到3D电影的观众便呵呵地笑了起来,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头,符合一个贺岁档电影应有的气氛。然后,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
电影有三个空间,现实的,记忆的,梦境的。镜头的长短,用以区分梦境和现实,而现实和回忆则用黄觉头发的颜色分辨。前一个小时,是现实和回忆的交织,镜头被剪得很碎,有时候一场戏只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身体动作,又跳到另一个时空。那是记忆突然蹦出来的样子,又提供了拼凑的某些线索。
如果顺着说故事,罗紘武更像是一个媒介,是串起往事的一条绳。从黑道大哥左宏元或者神秘女子万绮雯说起会更顺畅一些。
12年前,外乡女子化名万绮雯被一个叫老A的人骗到凯里,她利用左宏元杀掉老A,成了左的情妇。左宏元杀人时从另一位黑社会人员老鹰那里借了一把枪。老鹰的儿子白猫发现了那把枪和杀人的秘密想要勒索左宏元,却反被左杀害。为了追查白猫的死,罗紘武找到左宏元的情人万绮雯,因为怕杀人的事情败露,万绮雯谎称怀孕利用罗紘武杀人。罗紘武一心想要带万绮雯私奔,在电影院杀了左宏元后,却再也找不到万绮雯。

十二年后,罗紘武因为父亲去世回到故乡凯里,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,在停下的时钟背面发现了当年初次见面送给万绮雯的照片。原来万绮雯把照片给了她的朋友,一个卖假身份的女子。
通过照片的线索,十二年后的罗紘武拼凑出万绮雯的种种面目和生活轨迹。在去寻找万绮雯的路上做了一个悠长的梦,梦里的万绮雯还没有成为之后的蛇蝎女子,一头红发还是天真的样子。而和离家出走的母亲,半路离场的同伴,未曾谋面的孩子,这些生命中的羁绊,都一一达到了和解。
凶杀、兄弟、复仇、蛇蝎妇人、欲望、秘密,这些关键词常常是一部紧张刺激的悬疑片里的重要元素,但在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中,悬疑有了另外一种讲法,它是反类型、非线性、碎片化、迟缓而凝滞的,观众以往在类型片中获得的经验,在这部电影面前完全失效。
毕赣是有意在“破坏”类型片的叙事成规的。在采访中他曾说:“我先写的其实是一部黑色电影,类似于比利·怀尔德的《双重赔偿》。然后从每一场戏开始破坏它,从局部一点点地开始破坏,到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。”本来一两个模式化的镜头可以说完的事情,他偏用镜头的组织破坏掉——他渴望以更具想象力的方式抵达,让视听语言与众不同。

因此,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叙事顺序,有顺叙,有倒叙,也有插叙,它的整个时间轴是参差错落的,一会儿是当下一会儿是过去,回忆与现实交互错置,观众得从罗纮武的外貌变化(比如头发的颜色)来进行辨别。
其他悬疑类型片,会有清晰的目标、早就预设好的准确节奏,一切都循规蹈矩不会跑偏,但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,固定机位、特写、长镜头,大量的呓语、意象和符号,让电影的节奏慢下来,悬疑也因晦涩、暧昧和模糊,而愈发悬疑。
如果说影片的前半段尚有迹可循,罗纮武与万绮雯的相识、相爱、相离线索不至于让观众堕入迷雾;那么大约在剧情进展到70分钟左右的时候,罗纮武来到荡麦寻找万绮雯,在一家电影院坐下,掏出3D眼镜戴上,罗纮武入睡进入一段漫长的梦境,影片的后半段开始——这是一个3D技术拍摄的一个小时的长镜头,但这段梦境就真的是梦境,缺乏由来、逻辑不清,不少观众也开始迷失方向。
这是电影评价两极分化的最大来源,有人称赞为“导演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电影语言,胆大心细地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。他极为浪漫地告诉大家,有些电影只能在电影院看”,也有人严厉批评“如果通过镜头长短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导演能否载入史册的标准,我们家门口的监控录像可以拿奥斯卡了”。
初看之下,这是一部《路边野餐》的豪华版,有相似的意象和主题,也有相似的从现实入梦,长镜头释梦的结构,缺席的母亲,没能长大的孩子,入过狱的长辈,甚至港台流行歌曲元素。但它又是那么新,上天入地的长镜头坠入层层盗梦空间,把电影本身剥离故事的那部分影像语言发挥到了极致。

尽管毕赣自己也预见“这部电影会像外星人一样降落到他们的生活当中”。而事实上,如果真的有外星人,绝大部分人会把他当做怪物,未必会以积极情绪面对。
铺天盖地一星的愤怒,也可以想象这种尴尬吧,来看电影的大多是抱着“一吻跨年”目的的情侣,至少有一半的人是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怎么回事的来约会的。结果坐在电影里面一脸懵逼,不仅剧情看不懂,还疑虑重重要忍受来自另一半的嫌弃和白眼,万一是第一次约会,可能就直接因为这部电影直接变成“约会的最后一个夜晚”了。
诚然5000万成本的大投入可能不捅破文艺片受众的天花板破出边界去,要回本会很难,但这样的营销,是否对一个导演真正负责?当他找到属于他的观众,电影才能够得到公允的评价。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推到大众面前,承受无端骂名,下一次又是否会影响他的创作和下一部投资方对他的判断。
这是否是另一种对导演的过度消费呢?作为导演,毕赣最大程度的坚持完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。但这次错位的营销,应该能为文艺片的营销带来些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