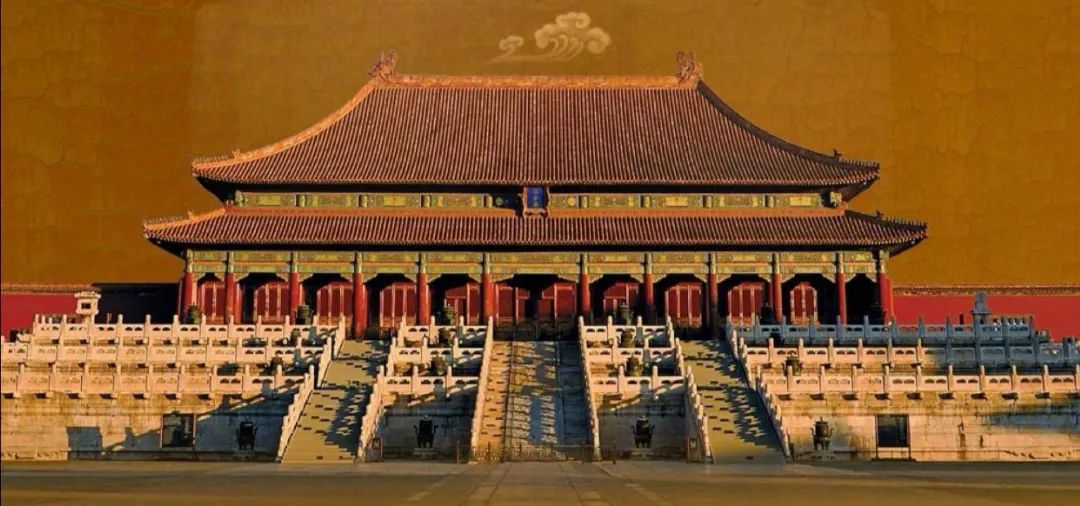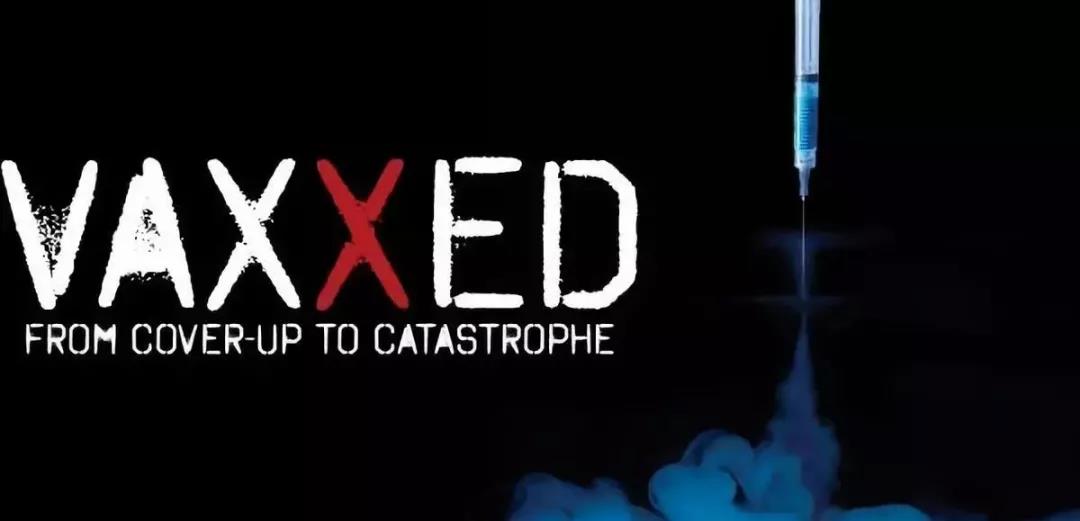《最后的棒棒》,中国首部自拍体励志纪实片。
军官何苦放下钢枪当起“棒棒”,用镜头记录做一年“棒棒”的经历。
1300元总投入,13集纪实片。
从2014年1月到2015年2月,一年零一个月,何苦靠着一根棒棒养活自己。
他摄像、撰稿、解说、编辑一肩挑,主题曲演唱也由他本人完成。
他用最简陋的装备,在最艰苦的环境,花最少的钱,拍出了“史上最接地气”纪录片。
如果我问你,一个人可以穷到什么地步?
你可能会想到在大学里,经济紧张的时候,曾经临时拿米饭配老干妈的日子。
可我要说的这些人,可以一年到头喝稀饭就着老干妈。
如果我问你,多久吃一次肉?
你可能会说,点个最便宜的荤菜外卖,最不济也会出现零星的肥肉花吧。
可我要说的这些人,把吃肉的次数严格规划到:每两周吃一次肉。
如果我问你,多久享受一次娱乐,比如追剧,比如看电影?
你可能会说,随时随地。现在拿着手机看综艺、看电影、看电子书so easy。
可我要说的这些人,唯一的娱乐就是报纸,或者是二手VCD放《刘三姐》《西游记》和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其中《刘三姐》可以看300多遍……

为什么我要做上面的对比?
因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。
他们并非是生活在偏远山村的人,而是身在发达城市里的“打工”人。
在重庆,在最繁华的解放碑旁边,有这么一群即将消失在历史长河的人
导演何苦,用纪录片记下了他们的生活。
“虽然旁白LN不分,虽然插曲真是难听,但仍然大大的五星”。看过的人这么说。
这是摄制组在自力巷租住的屋子,最低租金60元,何苦住的是300元的房子,就是照片里的这间。
何苦后来对媒体说:我租住的这间屋子,床是用木板纸壳拼的。窗户缺块玻璃,挡不住外面垃圾场飘来的腐臭味。因为有窗有电源,是条件最好的。“黑暗的走廊只能侧身通过,上楼的扶梯踩上去嘎吱吱响,感觉稍一用力,就会踩断坠落。”
为能深入体验生活,何苦拜65岁的棒棒黄师傅为师。
黄师傅说,“随便拿着棍子,找饭吃的是叫花子,找活干的是棒棒。这是最本质的区别。”
第一天,何苦跟黄师傅出门找活干,碰到一个人要送100斤涂料,走2公里路,工钱10块。
何苦自告奋勇接了这个活,结果先是小步快跑,接着举步维艰,最后肩膀疼得抬不起来。
黄师傅说,棒棒的力气不是养出来的,是压出来的。
回来路上,师徒俩又接到新任务,是近300斤的货物。
雇主说,花20元请俩人不划算,10块钱请一个人又于心不忍。
黄师傅说,你给我15块,我一个人咬咬牙干了,多挣你5块钱。
棒棒不光扛包送货,只要能挣钱,他们都会考虑。
雇主家舀狗粮的勺掉进厕所,找到黄师傅让帮忙弄出来。
黄师傅要20元,这份交易成交。
他跪在厕所地上,挽起袖子,担心弄脏外套。
先用几根手指挑出几张用过的卫生纸,又把胳膊往里伸了一点,从粪水里拿出掉进去的勺。
干完所有这些,黄师傅洗了三遍手。
雇主用手指夹着工钱,递给黄师傅,让他出门时一起将香皂扔了。
师傅满脸尴尬,照着做了。面对3天没有入账的现实情况,20块钱太重要了。
可遇到乞丐时,黄师傅还是没控制住伸出的手。
乞丐看到黄师傅身上背着棒棒,几次摆手拒绝好意,可黄师傅还是把钱塞在乞丐身前的罐子里。
何苦跟着黄师傅干了一个月,本来约定好第一个月所有收入都归师父,但黄师傅觉得这样不公平,所以一五一十地算着账。
何苦说:“我生平第一次对‘血汗钱’这三个字,有了感性的理解。”
黄师傅身上带着明显的时代印痕,也带有个人命运的深深镌刻。
因为出身不好,黄师傅处处遭到排挤和打压,到了30多岁还没找到老婆,后来遇到个有着好几个娃的寡妇,两人生下个女儿。
为养活孩子,他出门打工,寡妇却和别的男人跑了,把女儿扔给了他。
一波三折的命运让他很想向命运屈服,但女儿的存在让他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。
棒棒,一做就是30年。
十年前,他给女儿在自家镇上买了套140多平米的房子,为了还债,他继续在重庆解放碑附近卖力。
只在过年时,才会耗时1天,转乘5次,为节约6块钱回女儿家。
看女儿时,黄师傅还会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些,不想让她在婆家丢人。
西服套马甲,是他两件最体面的衣服,马甲套外面,是为了能让人看到。
然而,过完年回来没多久,棒棒们租住的自力巷53号即将被拆迁。
因为再难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,所有人下定决心要坚守到最后一刻。
一天早晨,上完公厕黄师傅发现,仅仅20分钟时间,整个家园变成废墟。
虽然提前一天已有人通知要拆迁,但这里从上世纪96年就说要拆迁,到今天都没拆掉,这增加了大家心里的侥幸。
黄师傅蒙了,他坐在废墟前迟迟不离开,因为自己有2300元的巨款被压在屋里,他担心被人拿走。
持续好几天,他每天过来巡逻。
担心财产丢失的压力,再加上原本就出现危险信号的身体,终于压垮了黄师傅。
因为没钱,黄师傅坚决不去医院,任由自己躺在地上痛苦呻吟。
老伙计们看不下去了,拿着向二房东借的最后20几块钱,带着黄师傅打车去了小诊所。
老伙计老杭不顾危险偷偷爬进废墟,帮黄师傅把2300块钱找了出来。
为此,右手被钉子划得伤痕累累,他从街道地上捡起一个废弃的白色塑料袋,包扎了起来。
尽管贫穷一直笼罩着自力巷53号,但有些东西,他们似乎并没有丢失。
人总在受尽苦难后,依旧向往生活。
身体每况愈下的黄师傅准备回家养病了,老伙计都来送他。
棒棒们都曾是自力巷53号的住户,也都在经受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双重拷问。
河南,因来自河南而得名。
因为多吃了两个鸡蛋被大排档老板解雇,所以想要通过打牌赚钱,结果输光了所有钱。
咸菜配剩稀饭、面条配老干妈是河南每天的饭食。
另外两个棒棒老金和老甘多年来一直是搭伙做饭。
老金常常能吃到老甘从大排档客人吃剩下的盘子里捡的串串。
老甘说,“我捡东西有原则。只捡完整的一串,这样干净。”
“精打细算,省吃俭用”这八个字,在棒棒里被运用到极致。
比如老金,他卖了四袋瓶子,换了部二手手机,还办了个每月28元的套餐,每个月他都会精确地用光套餐里的通话分钟数,他说这样才不浪费。
老甘说,人饿不死,人是活的。
这是在艰难情况下,依旧要迸发出的自信。
活着就是要怀着希望。
老甘在夏天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期,除了做棒棒,他尽力捡瓶子赚钱。
他会在一大袋瓶子里,用水装满1、2个瓶子用来压秤。
如果被发现,他会装作是找到了自己装水的瓶子。
同样是捡瓶子,一袋子他能比别人多赚1、2块钱。
在老甘的这些小聪明里,渗透着深深的无奈。
老甘是求变的代表,煮猪肉没法用电饭煲,他会转用热水棒,成功达到目的。
一个人,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,为了生存和生活,都会做出这样那样的改变,也许这就是生存的本质。
棒棒老杭年轻时,老婆跟人跑了,他决定进城打工,但命运接连和他开玩笑。
第一个五年,他攒了10000块,却在路上被人偷了。
第二个五年,他攒下25000块,小偷从他床头把钱给偷走了。
后来,他仍旧常被人骗。
他找人算命,被告知60岁时会转运,于是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60岁生日上。
当人绝望时,总要有点希望,这是一个人必须要有的精神寄托。
对穷苦的生活描述,并不是何苦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,既然叫《最后的棒棒》,他就要把这些人消失的路径拍出来。
片中,好几个趁势找机会转行的棒棒,都谋求到更好的生活。
在五一路口,毛土豪从棒棒进入家装行业,开始积累财富,最后带着全家人搬进新房,得到阶层的跃迁。
何苦因一次意外,成了包工头。
思维和眼界得到改变,招募到许多棒棒兄弟帮他干活。
何苦给棒棒兄弟每天150块,自己也能拿到300块。
值得一提的是,雇佣他们的老板,在年轻时也曾做过棒棒。
可有些人,却似乎注定要被时代抛弃。
因为年迈,他们已没有太多机会学习,等待他们的只有勉强混口饭吃的活计。
比如即将60岁的老甘,看到别人跟何苦工作,他还是坚守着管吃管住一天40元的大排档工作。
他已冒不起风险了。

不止棒棒,还有很多行业也在消逝着。
因为全国都在推行殡葬改革,棺材行业就像棒棒行业一样告别时代。
给棒棒老杭做棺材的年纪81+72的组合,是目前镇上最年轻的棺材匠。
除了棒棒,还有很多我们身边曾经出现过的职业渐渐淡出了视野。
技术的进步和工业效率的提高让很多职业变成历史,甚至目前正旺的职业,也会在未来成为过眼云烟。
一个地方的拆迁,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进程。
一个职业的没落,代表着社会劳动力的进步。
一群人的生活经历,代表着万千人的生活状况。
以棒棒为代表的一代人,背负着历史的沉重负担,面临着人生中的诸多不幸,但他们仍凭借一身力气赚钱养家,在他们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生之笑脸。
有人说,中国人向来能吃苦,其实这吃苦的背后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《最后的棒棒》向我们展示着一种城市化过程中,波及所有行业、所有领域的阵痛。
在祭奠着一些即将消失的行业,和一些不会消失的人的精神。
在棒棒栖居的陋室四周,发达的城市正在像野草一样离离上窜。
棒棒终将消失,很多职业也终将消失。
好在,只要是存在过的,就会永远被放在那里,被记忆着。
也许就是这么一群棒棒,给我们展示了最真情的生活,演绎了最真实的生存。
他们的经历与生活教我们明白生活的真意,体味到生存的艰难。
无论生活多么艰辛,道路多么坎坷,人们都要充满希望的活下去,都要寻找到奋斗的动力。
生活并不完美,上天更没有那么多的公平,但是我们的目标都相同:
好好活着,为了更好的生存。
这是人的基本权利,也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。
帕斯卡尔曾说:人是会思想的芦苇,这些坚韧不拔的人,终将在寒风过后,以新的面貌蓬勃生长。
是的,大寒过后,一定立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