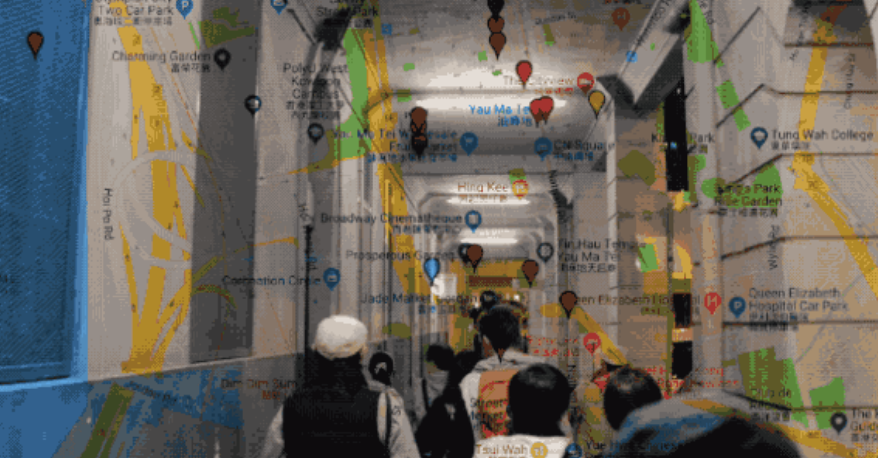“我是新裤子的主唱彭磊,我是著名导演。”
——这是彭磊在微博个人简介上的自我介绍。

33支乐队刚刚集体亮相,《乐队的夏天2》今天又开启了第二轮的激烈对战。舞台上的他们摇滚十足,肆意打造着自己的音乐,舞台下,除了音乐,他们也将这份炽热献给着另外的事物。比如电影。
今晚最新播出的节目里,椅子乐团初次听到《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》,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德昌导演的《青梅竹马》,因此决定将这首歌改编为“有山有海兜风”的感觉;第四期,超级乐迷周迅称赞达闻西乐队演唱曲目的歌词时,主唱/吉他手猴子也提到杨德昌导演电影对乐队创作的影响;五月天、黑豹乐队前主唱秦勇、花儿乐队前主唱大张伟、还有年少玩过乐队的朴树,都在电影里贡献过自己的演技;上一季乐夏冠军新裤子彭磊,水木年华卢庚戌,短暂组过Z2乐队的张亚东,还亲自下场拍过几部电影...
这批“摇滚人”,或者更准确的说是“乐队人”,除了对音乐的偏爱,对电影也或多或少怀着一丝热爱。当乐队撞上电影,他们又会玩出什么样的火花呢?
爱电影、演电影、拍电影,
乐队人的“电影情结”
实际上,同为艺术,音乐和电影本来就是很多“文艺青年”的精神领地。玩乐队的“摇滚人们”,也不时透露着心中的那丝电影情结。
一代摇滚老炮崔健曾在采访中提到,电影是他音乐之外唯一的爱好,而且从小就喜欢看电影,各种风格都爱看。去年走红的盘尼西林乐队,主唱小乐也表示,“盘尼西林”这一名字的由来,就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看战争、历史一类的电影,了解了青霉素(盘尼西林)对降低人类死亡率的贡献,所以比较意识流地选用了这个词,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像盘尼西林一样治愈大家。
当然,他们还会将从电影里获取到的灵感反馈到音乐创作上。《乐夏2》里,达闻西乐队一曲《大都会》,让周迅颇为动容,表示在歌词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主唱猴子转而提到杨德昌导演所赋予的创作影响——“我特别喜欢杨德昌导演的电影,很喜欢他那种叙事方式,如果不仔细看的话,感觉跟看纪录片一样,特别平实、客观、克制、冷静,不是那种直给的。”海外的天空大爆炸乐队在国内演出接受采访时也表示:“看电影是一个巨大的(创作)灵感来源...把所有难以解释的事情通过做成音乐,来表达我们的情感。”

▲达闻西乐队
而为电影创作或演唱宣传曲是很多乐队人参与电影的一种方式。去年刺猬乐队走红后,立马就被《跳舞吧!大象》请去演唱了那首《火车驶向云外,梦安魂于九霄》的代表作;《无间道2》里的那首《长空》则是Beyond特意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曲;窦唯(《李米的猜想》)、左小祖咒(《西虹市首富》)等等更是当下电影配乐届的常见身影。
除此之外,很多乐队人还化身演员直接演起了电影。不过,这其中,具备自传或记录性质的纪录片、演唱会电影还占据着不小的部分。如五月天(《五月天追梦3DNA》)、崔健(《超越那一天》)都将自己的音乐作品转到电影市场,用电影的形式呈现给了更多观众。相比于专业演员,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更多是“本色出演”。
抛开这一类,乐队人出演电影主要还是以客串为主。像五月天就团队出演过一部《五月之恋》,电影讲述的其实也是两个五月天粉丝的爱情故事。主唱阿信还在《近在咫尺的爱恋》中饰演了一位不苟言笑的选秀评委,称得上是一次独立的个人演戏尝试;花儿乐队前主唱大张伟则客串过《东成西就》《越光宝盒》等作品;大鹏自编自导自演的《缝纫机乐队》,更是汇聚了beyond乐队黄贯中和叶世荣、原唐朝乐队刘义军、黑豹乐队赵明义、痛仰乐队高虎、超载乐队李延亮、面孔乐队欧洋、新裤子乐队彭磊等一大批乐队人。

▲《缝纫机乐队》客串乐队人
当然,其中不乏扛起主角大任的乐队演员。朴树就和周迅两度合作,主演了《如果没有爱》和《那时花开》两部作品。黑豹乐队的第三代主唱秦勇,还凭借《走出尘埃》获得上影节亚洲新人奖的最佳男演员。
对电影最有诚意的自然还要属真正实践拍电影的那群人了。新裤子主唱彭磊便先后创作了《北海怪兽》《熊猫奶糖》《乐队》《房间里的舞蹈》等多部作品,其中,他还凭借《乐队》拿下了上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;水木年华卢庚戌也执导了《怒放之青春再见》和《一生有你2019》;“青铜器乐队”高晓松则拍摄了《我心飞翔》《大武生》等作品,前面提到的《那时花开》也出自他之手;还有崔健的《蓝色骨头》,郑钧编剧的《摇滚藏獒》,张亚东执导的电影处女作《湖边密林》还曾拿下上影节创投单元“最佳创意项目”奖,但目前还未上映。

从单纯的爱电影,参与音乐创作,到演电影、拍电影,乐队人逐渐地在电影圈占下一席之地。但对部分人来说,他们对电影的参与更多是被动的,比如被邀请来创作、演唱或者演戏,其本身并没有太主动强烈的参与欲望。当然,这其中不乏真正想要到电影里尝试体验一把的人。
生活、挑战、梦想、“撩妹”...
乐队人的电影初衷
因为父亲的离世,曾经叱咤风云的摇滚歌手决定退出乐坛,人到中年的他逐渐褪去了往日激情,过起了见招拆招的忙碌生活——《走出尘埃》的故事几乎是为秦勇量身定做。不过,对于这样的巧合导演早就做了辟谣。但这样的相似经历还是让秦勇有了更大的底气去尝试演员这条路。
当然这背后还有无奈的生活压力的驱使。其实,除了父亲的离世,儿子被确诊感统失调症也是秦勇当年隐退的原因。那些年,为了照顾家人,他开过家具厂、卖过快餐。即使因为小时候对样板戏的固有印象,秦勇对演员一直怀有特殊情绪,认为演戏是虚伪、假大空的,“长大以后,由于生活压力和经济情况”,他还是想要去做这件事。

▲《走出尘埃》秦勇
最重要的,这部电影还是他献给“影迷”儿子的一份礼物:“儿子特别喜欢电影,他的口号就是‘我要当导演’。我想你要学音乐,我可以帮你,学导演,父皇根本就摸不着边。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,能让孩子得到帮助,所以我就非常努力。”
而在郑钧眼里,自己所有的跟歌手无关的尝试,包括拍电影,都是不安全感使然:“我一直以来干的事都是不安全的模式,因为我就是这么长大的,我是一个从小就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重复着生活的人。”不过,与其称之为“不安全感”,倒不如说是喜欢迎接各种挑战。这也是秦勇的人生信条。
对卢庚戌来说,做电影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和热爱。尤其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积淀后,自己也拥有了表达的欲望。当然,音乐也是一种表达,但在他看来,和电影比起来,音乐的容量就显得有些不够了。张亚东也提到,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,电影可以多层面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。“这几年我一直在尝试影像方面的创作,无论摄影、广告、MV、短片都给了我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。以前我用耳朵,现在用眼睛,这是一个延伸。做影像能让我重新思考做音乐时的很多东西,这是个相互刺激的过程。”

▲卢庚戌与高晓松
而高晓松对电影的热爱甚至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。当年,还在上大三的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当科学家,毅然决然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退学,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电影,但最终他还是没能考上北电。但拍电影的这颗种子却在他心里种下了。
除此之外,还有其它比较“摇滚”的因素使然。彭磊就坦言最初是发现玩乐队没法吸引女孩子的注意,受到校友贾樟柯的“启发”后才决定去拍电影,又或者是为了让他斥巨资(2.5万元)买来的DV机发挥起它的作用,不至于闲置,才有了拍长片处女作《北海怪兽》的想法。当然,这或许又是他的一番“彭言彭语”。
观众评分、市场票房,
好电影不只靠“一腔热血”
从玩音乐到“玩电影”,不同内容创作背后也是乐队人的一次跨界尝试。既然是跨界,创作过程难免“不专业”,电影作品的最终呈现也会略显稚嫩。彭磊就曾提到,拍电影的时候从来不聊剧本,都是自己一个人弄。卢庚戌也表示在最开始学写剧本时,只看了一本名为《21天学会编剧》的速成书。
实际上,以上提到的各乐队人大部分都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。高晓松还曾到北电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过电影,彭磊虽然是北电毕业,而且出自明星云集的96级,但学的其实是动画专业。在执导经验上,不少人倒是给自己的乐队拍过MV或短片。转到电影创作上,他们往往也会不自觉参照之前的习惯进行创作。因而,在关于这些电影的评价里,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观众说“像看超长MV一样”,甚至不乏“好好回去做乐队”的评价。

备注:1.表格仅从目前有乐队或曾组过乐队的乐队人出发,统计了他们曾经主演、编剧、执导过的作品,如有遗漏还请指正;
2.排名不分先后,数据来源于豆瓣、猫眼等平台。
拍sir也就乐队人主演、编剧、执导的作品做了不完全统计,从豆瓣评分维度出发,观众评分最高的是五月天的3部系列电影和崔健的《超越那一天》,从类型上都属于演唱会作品。虽然电影在讲述过程中都穿插了几个小故事,但他们的角色都还是自己。此外,还有882位观众给彭磊的《北海怪兽》打出了7.2的成绩,高晓松导演、朴树和周迅主演的《那时花开》则有7分。但大部分都在7分以下。
而能够查到具体票房数据的几部作品基本都是千万及以下的成绩。其中,去年上映的《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》有着超五千万票房的表现,《一生有你2019》和《大武生》则在四千万以上,票房最低的是《摇滚吧!老爸》,仅有着六万的数据。
在中国电影市场逐渐扩大,影片动辄几亿、几十亿的大环境下,这样的票房成绩或许不值一提,但并不意味着“无利可收”。五月天经纪人谢芝芬就曾表示:“《DNA》巡演开了44场,观众人次有100多万,《诺亚方舟》开了71场,统计的观众数据是248万。正是因为有之前那部电影的推广,吸引了之前没看过他们演唱会的人,所以五月天的《诺亚方舟》巡演才能做到71场。”当然,票房坚挺背后也体现着五月天本身的音乐和受众影响力。

▲《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》
而面对票房失利,郑钧曾对自己有过怀疑,但从来没有后悔这样的尝试——“中国电影行业让我感到很伤感,一直认为好好做事就可以,但当头一棒让我学会很多东西。其实中国电影有庞大的系统和游戏规则。”对于之后是否还有拍电影的计划,他表示以后再说。
2012年,彭磊在上影节颁奖礼现场喊道:“我肯定会努力为国产电影尽份儿力的,我一定要拍一部对得起所有中国人的电影!”但除了隔年的《房间里的舞蹈》,他再没有推出其它作品;企图做电影明星的朴树在拍过几部电影之后,从来没有接下过另一部,而且还将这段经历笑称为“人生污点”;卢庚戌在历经两次不太成功的青春题材尝试后,决定“以后要做一个自己擅长且更有表达力的东西。”
不管是暂停还是继续前进,可以确定的是,一部好电影的出现,并不是一腔热血就能实现的。电影创作更需要扛打的内容核心和完备的制作体系。而从“跨界人”到真正的“著名导演”,也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。